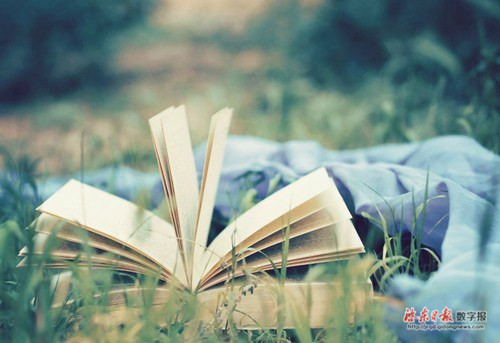走近记忆
蒋长云
我命硬,“克”母校!
但凡我上过的学校,原址上都没有了朗朗书声,要么被拆迁,要么被合并,要么连校名连校舍直接湮没在历史和麦田中。
我生于乡野,天资也钝,所以没上过什么好学校。这话挺对不住我的那些母校的。但事实就是事实,相信那些母校不会因此而怪我。她们多数和我一样草根,苟苟且且的,应该也从未做过百年名校的梦。
我的小学早已停办了。那小学虽小,名字却颇具古风——唐虞小学。对,唐尧虞舜的唐虞。一个早上,我在地摊书市上看到一副对子“满架诗书小邹鲁,一家和乐古唐虞”。邹鲁,孔孟故乡、圣贤之地,唐虞与之相提并论,多么高大上。我觉得甚至比清北复交浙科南的名字都牛。我突然特别想对周边人夸耀说,这文绉绉的对子上有我母校的名字。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一个乡村小学,叫这个名,本身就有点僭越。好比一个朴素的村姑,偏叫了“杨玉环”,总归是有点别扭的。虞字笔划有点多,当年邮递员分报纸图省事,经常在报纸上写成“唐2校”(启海话“2”与“虞”音近),“唐2校”原址上现在是一个米酒作坊和一个一丁点小的针织厂。针织厂所在的位置,当年是操场,也是全大队的文化广场,大队开社员大会,放露天电影就在这里。这里也是我们的广阔天地,一个漏气破篮球可以满头大汗追抢半天。小学毕业那天,大雨初歇,操场积满了水,很浑浊的水。我在浑水里淌来淌去,送别一个个同学,我第一次有了离愁别绪,有点哽咽,久久不愿离去。唐虞校离我老家也就一河之隔,很近,但那积满水的操场已然很遥远了,再也回不去。
我上的第一个初中育新中学,现在只剩下记忆中的名字和田间的几段断垣残壁。第二个永阳中学,校园也已废弃,因为围有小河和大树,成了鸟的天堂。据说,现在有很多珍稀鸟类常年盘旋于此,间或有摄影家慕名而来拍鸟的大片。我见过几张,模糊的背景里就有我熟悉的老刺槐树和校舍的模样。人家都夸这鸟精神,这照片拍得好,焦距调得准,背景虚化得恰当。我则五味杂陈。我的母校,当年熙熙攘攘、钟声悠扬的母校,现在确确实实“门可罗雀”,被直接当作了飞禽的背景,还被虚化了。我的众多在北上广深的农民工兄弟,和出息了做了包工头的老板同学,见母校沦落至此,不知作何感想?
我的高中母校汇龙中学还兴盛地存在着,只是早已经退城进郊了。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汇龙中学就在现在的名都苑南区的位置。唯一的大门对着人民路。校区极小,施展不开,有的班级做课间操要上楼顶。“鸡蛋壳里做道场”。一到课间人声鼎沸,耳边总是嗡嗡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职业教育甫兴,汇龙中学开风气之先,开办了电子班、财会班,还有幼师班。清一色女生,叽叽喳喳的,一群养眼的百灵鸟。学校的东南角是操场,操场的东南角有个琴房,那是姑娘们弹琴的地方。我们的体育课经常伴着悠扬的琴声。那时的汇中隐居闹市,招的大多是县城的孩子,时尚、前卫、自我、感性、热情、开放、调皮,像我这种农村的孩子进入汇龙中学,是名副其实的“升”学,得到了很多认知上的启蒙和观念上的突破。不夸张地说,汇龙中学在很多方面重塑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知识视野、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审美情趣、甚至性格等等。汇龙中学如今的新址我还没有去过,听说教育成果斐然,升学率等方方面面都挺好。但我仍固执地认为,如今优秀的汇中与当年我的母校肯定不是一回事,无论核心价值、还是腔调面目,应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学校。作为我母校的那个汇龙中学,就好像人们常怀念的八十年代一样,已经远逝了。现在的汇中课间操时还跳学校自创的变节奏操么,还在中学生各类体育比赛中一骑绝尘么,有学生去乡下跳霹雳舞挣外快么,有晚自修课上学生下象棋、巡查老师倚窗悄悄看了半天忍不住支臭招么,有学生自带音响在自习课上给全班同学放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么,有翻围墙看电影的么,有把政府的吉普车偷开到体育场去的么,有牵着大狼狗上学直奔校长室的么,有烫大波浪、抹口红、穿裘皮大衣高统皮靴的摩登女生么,有在课间去对面新华书店顺一本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看后又还回去的么,公告栏里还几乎不间断地有处分通报么……请不要认为我在诋毁母校,当年我的母校就是这样生猛。如此生猛的母校培养出了大批生龙活虎留在本地建设家乡的优秀劳动者,更有改革开放初期的公派留学生、欧盟钢铁专家、“好八连”连长……还有年过半百、仍经常日骑自行车上百公里的文联主席等等许许多多有趣的灵魂。汇中三年是我学生时代最难忘的岁月,能上80年代的汇龙中学,可以说是我一辈子的荣幸和骄傲。
我的另一个母校江苏银行学校已并入南京审计大学,如今有地铁与南京主城相融,是一个比较热闹美丽的地方了。当年,这里很偏僻闭塞,好似山坳里的一座小庙,更有点像《围城》中的三闾大学,离江浦县城也有二十分钟的山路。学校小,学生少,也因此有了静谧之美,隐逸之美。学制才两年,去头掐尾,包括中间的种种变故,实际在校时间只有十来个月,印象比较有限和模糊。零星的记忆片断有:加入了120人的大合唱团、参与在宁高校纪念“五四”70周年歌咏比赛,一个月的排练过程非常嗨,一个年过半百的音乐硕士给我们普及声乐知识,以至我现在都很喜欢合唱。学校艺术节听一个叫贺东久的词作者讲诗歌,看林散之的入室弟子写书法(草圣林散之是江浦老县长,江浦有很多林的印记)。到班主任家去吃馄饨,新婚的师母是个温婉的幼师,养了一只纯白的猫。系主任业余教授“一指禅”,知我感冒,发功助我康复。约了几个同学去县城看电影,月夜淌溪而归,清凉的山泉拂过脚背,激起女生娇嗲夸张的尖叫……2013年我班同学专程回了一次江浦,欣喜地发现银行学校的一切都原样地保留着,很安静地历史感地存在于南审一隅。校舍空着,不用也不拆,可能也是为了让那些行长学子们回来有怀旧的场所。我们回到了自己住过的宿舍,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想往事。那年暑期结束返校,兴化的兄弟兴冲冲破门而入,从挎包里倒出一大堆碎票。那两天兴化发大水,抓了好多鱼,他上车前正在市场上卖鱼。我们一起帮他整理湿漉漉带着刺鼻鱼腥味的钱。他后来用这些钱买了一台红色的收录机。从此以后,我们的宿舍就象书店的音像厅一样,整日浸泡在最流行的歌里。“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这样的旋律,现在不用按“播放”键,随时随地都能细致精确地在耳边回响。而那天,面对空荡的宿舍,在我耳边回响的则是杨庆煌那纯净大男生的声音“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会轻轻地按你的门铃,不管清晨,还是黄昏,请你为我点一盏灯……”又是8年过去了,银行学校的背影是否还挺拔着,是否仍能为我点一盏灯。
常见人在微信群里发自己高大上的母校照片,百年校庆啊,风景如画啊,诱人的校园美食啊。那时,我会很沉默。我也会偷偷想起我的那些校运不昌的可怜母校,尽管她们已然只存在于记忆中,大多连留念的照片都没有了,但毕竟也真真切切给过我呵护和滋养。我对她们的怀念和挚爱,跟那些给著名母校捐了许多钱的豪商巨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因为母校的沧桑之变,而更加苍凉、沉郁和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