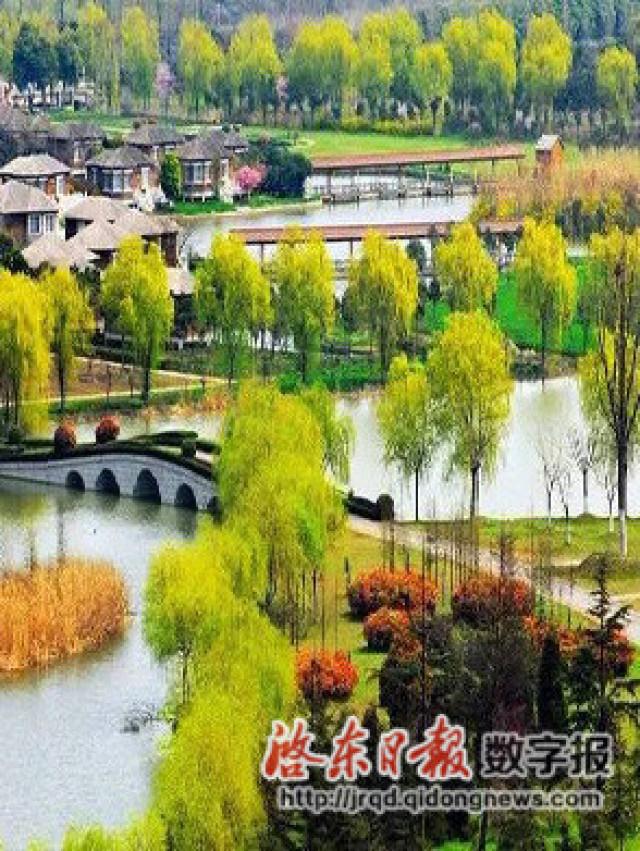
东疆掠影
张永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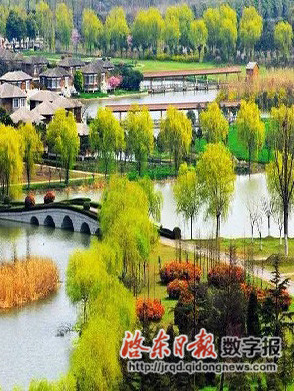
欣赏秋天,选择一条路很重要。
这是一条乡级公路,叫“兴糖路”,不是高速公路,但同样有两边的金属护栏,同样有双向分割的实黄和虚黄线,也同样有沥青、砂石、石灰、泥土混合滚压成的质地。她在两条一字排开的埭中间,显得有档次,有品位,她连接了城市的喧嚣和农村的安宁。因为是新的,开通不久,走的人不多,喧嚣也少,所以我便开始选择经过这条路上下班。这样的路上,可以放缓速度,可以静下心来,可以远眺,可以近览。甚至可以停下车,装一回幼稚,演一下童真,总之,随心所欲。
白天的路上空啊,有忽高忽低的白云。静的像鱼纹,像小山,动的像奔羊,像跳鱼。纹丝不动的是蓝天,像是倒立的大海,白云就是浪花,仰头看一阵也会眩晕。我九岁时跟父亲出海,我跟父亲说这船怎么一直在航呀?父亲笑着说,你晕船了,船分明停着呢。固然,有几个渔民在把网的一端系在滚筒上,准备卷起沉甸甸的塞满鱼蟹的网兜呢。船停了才可以干活,而我依然认为船在海浪里前行,大概是饥晕交加,于是父亲让我吃下中秋剩余的两只月饼。我现在走在兴糖路上,也像是小时候坐在父亲和其他渔民合买的那艘“宁波”船上,醉了,醉了,像喝了一瓶低度但有后劲的米白酒。
路边的秋景像是下酒菜,也是醉料。依河而建的路的旁边,有河坡谢叶的黄豆,有红绿相间的石楠,有一望无际的下垂熟谷,有染了黄发的水杉、银杏,还有羞见路人、飞入小林间的白鹭等等。这里没有高大的树木,却拉近了与大田的视觉焦距;没有密集的居民房,却有了“烟村四五家”的感觉;没有声嘶力竭呐喊的知了,却有了秋日新的“管弦乐队”。
路边原本闭塞的几个河边人家,忽然间堂前路开,一如归隐南山的修禅人突然间又暴露于世人前面,想低调都难。于是,这些人家一改以往的腼腆和内敛,檐头下、山头边、墙根头垂悬着丰收的样本,堆放着形态各异的南瓜,盆栽着深红色的鸡冠花。扁豆花也被像主人宠溺着似的窜满了篱笆架,我似乎闻到了扁豆饭的那种香味。没摘下的老丝瓜依旧挂着,等待着变成一种新的存在价值——刷锅碗的天然清洁球。
喜欢这里的秋天,还是因为这里同时拥有三种苇,一是芦苇,二是芦竹,三是蒲苇。同是禾本科,但是各具特点的,各有各存在的必要。先说芦苇,那是以前普通但很实用的河边植物,现在只存在于少数的沟头河梢,除了端午节期间的芦叶被争宠,其余的时间里就是被晾着的失势“小主”。芦花由青转灰,再由灰转白,最后絮花落尽,光秃秃的芦苇杆被简朴的人家当土灶的燃料割走或是被就地付之一炬。看着秋风中的灰色芦花,我想起了以往的人们系着腰兜采芦花的情形,祖父的表兄曾经从吕四徒步走到我的家乡采芦叶,但这个固执的大爷爷谢绝了当时在世祖父母的用膳邀请。芦竹质地坚硬粗壮,在秋风中依旧昂然挺立,继续承担着制作篱笆杆的功能。蒲苇是我从“识花君”的软件上搜索到的,这种蒲苇估计是兴糖路建设时引进的,据说产自南美。花头很好看,挤挤挨挨地簇拥在一起,这长长的花绒看着就温暖,很有别于前面两种苇的那种高贵气质,难怪蒲苇的花语就是“奔放的爱”。
还有这里特有的植物饮料——芦稷,有城里回乡的青年男女,走着卖弄秋骚的步伐,肩扛芦稷,像是鸬鹚船上渔翁担的划水竹竿。然后放下,大大方方地捋掉叶子、去掉穗头、斩成段,塞入轿车的后备箱。
暮色下的兴糖路,更加的恬静,让人心安,促织们弹着乡野梦呓调,像催眠的小曲,在耳畔边绸柔般滑过。像潺潺的流水,在秋风里自然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