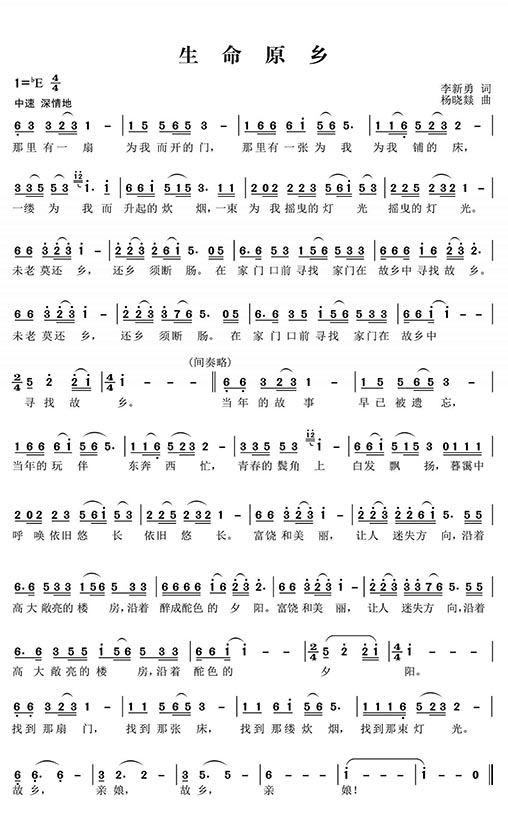硕果 项亦周摄
惠萍镇简介
为纪念1947年4月28日牺牲的崇明籍共产党员朱惠萍烈士,1957年,经启东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惠萍镇”之名正式启用。该镇位于江苏省启东市东南部,南靠长江,东临寅阳,西接启东市政府驻地汇龙镇,北至东海镇。镇政府驻地惠萍镇。全镇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具有海洋性与季风气候的双重特性,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崇启大桥纵贯全境,植物、渔业资源丰富。
秋日邂逅水果小镇
黄丽娟
近日读雪小禅的《七月半》,她说,天气微凉了,酷暑终于过去了,风力有秋意了,院子里的石榴结了果,亭子中的老人们打牌、聊天,池塘里睡莲开得正好。文字轻描淡写,却不乏秋意盎然。秋,如此盛美,岂能辜负它的馈赠呢?那么,就请你跟随我的脚步走进惠萍水果小镇吧。
沿沿江公路往东,来到惠萍镇大兴路口,“水果小镇”显目的门头便映入眼帘。路两边已有不少水果摊位,一张张淳朴的笑脸面前,堆满的是黄澄澄的梨、紫莹莹的葡萄,偶尔还有金灿灿的黄桃,令人垂涎。进入充满童话色彩的大门,一侧是宽阔的河面,清澈如镜,一侧是连片的果园,沁人心脾。
秋风中不时飘来丝丝果子的甜香味,我们迫不及待地往果园里钻。长长的竹篱笆走廊一直延伸到果园深处,两座凉亭安静地立在那里,飞檐翘角,给拙朴的农家果园增添了一抹江南园林的色彩。长廊里还设有座位,若坐于其间,品尝着随手就能摘到的水果,夕阳正红,风吹过来也不恼人,日子该有多惬意!
抬眼望,除了掩映在果林之中的农家小院,其余都是成片成片的果树,有桃、梨、橘子、枇杷、石榴等数十种水果。现在正是水梨丰收的季节,郁郁葱葱的梨树上挂满了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一层油亮的金黄。有些梨子熟透了,等不及采摘,从树上滚落下来,时间一长,泥土里便氤氲着水果醉人的芳香。同行的文友笑着说,这是葡萄酒的香气。嗯,坐对一棵果树,来一杯自酿的葡萄酒,真是极好的。
为了方便游人进园观赏采摘,果园里通有多条小道,有往梨园的,有往桃林的,也有往枇杷园的。你可以任意行走,不必担心会迷路,尽情享受自采自乐的田园生活。果园的东侧是一条蜿蜒的河道,这里即将完成游船码头建设。游船码头启用后,游人可以乘船沿着2000米长的小庙港河以及鲜果采摘区内8000多米的沟河系赏景、戏水,甚至可以伸手采摘沿岸的各种水果。
与丰水梨园相邻的则是桃子、蔬菜和草莓等种类繁多的果蔬种植园,到了成熟的季节,这里将为游客开放,提供赏花、摘果等服务。听水果小镇负责人介绍:“在果园南侧的水域地区,虾塘、蟹塘、鱼塘等垂钓区也已经建设完毕,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游玩项目。希望每一位来到小镇的游客住得舒心、吃得放心,真正让他们享受到不一样的美丽小镇风情。”
水果小镇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三八果园”在果园村正式成立。我们小时候听闻最多的就是“三八果园”,都说“三八果园”里的水果最好吃。至于为何得名,从未深究过。在果园中闲庭信步,偶遇一老妇,刚采摘完水梨,两手各提一桶沉甸甸的梨子。老妇告诉我们,这是黄花梨,每年到八月二十多号就可以采摘了。若是采得晚了会烂掉,若采了来不及卖也会坏。我问她之前还有些啥品种的梨,她掰着手指如数家珍:“丰水”“幸水”“新水”“新高”……原来,不一样的品种就会有不一样的成熟期。正当我们对她的梨啧啧称叹时,热情好客的老妇已挑了两个最大的梨塞给我,笑呵呵地说:“尝尝,这种梨水分足,甜,自家长的,不稀罕。”谢过老妇,我们顾不上用水冲洗,拿起梨子就啃,真的又脆又甜!
春有百花秋有果。我不禁想,若是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来到水果小镇,那这里定将会成为一片花的海洋吧——千树万树的梨花,白得似雪;成片成片的桃花,粉得似霞,一只只蝴蝶、蜜蜂快乐地来回穿梭,花香熏醉了游人,也熏醉了勤劳的小镇农民。
水果小镇不仅拥有优质的水果资源,它的地理位置也很占优势。濒临长江,紧靠崇启大桥,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大批上海、南通等地的游客前来观赏、度假、休闲,体验别样的农家乐,给水果小镇带来了勃勃的市场生机。水果小镇将成为以“万亩果园、江海人家”为主题,结合启东民俗文化、沙地文化,全力打造的一个乡村旅游品牌。
明年,待到春风起,咱们相约去水果小镇看花吧!
书法(薛刚)
小镇的“果园经”
倪静洁
惠萍有个“水果小镇”。这名字,让人感觉快乐又天真。八月底一日午后,在那里停留一个小时,只能算是惊鸿一瞥,但就此,映了心扉,着了念想,恰似“有美人兮,见之不忘”。
三步弓宽的径路一侧,有条清河似练,脉脉向南。岸边,有一座簇新的五阶梯二折弯的原色木桥码头。径路的另一侧,视线长抛处,一天一地的明田果树,繁枝浓叶,泻碧千里。近观则是肥叶成阴子满枝。八月饱满的黄桃水梨脆李傲挂枝头,灿如星辰,几只慧鸟点腾轻跃,人近也不惊。空气清甜甘洌,是氤氲香氛。这便是水果小镇的灵魂所在地——毗邻相连成绵延之势的一家家昌盛果园。
我们一行走,低调内敛,但还是招来淳朴好客正往返于果园劳作的果农们的本真款待。特别可乐的是一热情爆棚的中年农妇。
她正颠着节奏推一驾装满梨子的三轮,竹棚长廊里,我们“狭路相逢”。
伊停下,弯眉细眼地冲我们笑,指指我们正经过的果园区域,爽爽地招呼:这是我的果树呃,你们挑了摘了尝哟!
我们见她有趣,便合围问询,她便哒哒哒快板般如数家珍:我们这儿的梨哟,有“黄花”有“新世纪”有“清香”有“脆桂”,更有浙江农科院引进的“三水一高”!我们果园呀,六月枇杷黄,七月蜜桃采摘忙,八月梨子李子撂满筐,九月橘子堆来像小山样!
“那您整天累月劳作着辛苦不?” 我聆听着她的快言快语,随口一问。
于是她便又啪嗒拉开话匣:“习惯了呀,开心。产量高,收入好,又有乡里各种规划各种指导,建了码头咯,游乐场也正在建,上海人经常直接开车来买,销售真个越来越省心。我们呀,夏秋当里,田里开个早工晚工,风凉咄咄。我么,喜欢拿个小桶,装只充电收音机,挂了树上,一边听听沪剧越剧,一边跟着唱唱,用斜凿挑挑树上害虫子,省力咄咄个呀。我们村里的女人,不打牌不跳舞,也不喜欢穿了洋蓬蓬,就喜欢果园里做做生活,看看树叶越来越黑油油啊拥啊拥,看看果子一天换眼一天,就觉着开心。一天天忙碌抖抖,哪怕树根头种种南瓜也是开心个,南瓜藤瞎爬呀,就把它的头拽下来,让它爬在地上,既不影响水梨桃子,又可以正好黑掉乱草,一举两得个呀,结着红南瓜么,做做南瓜饼,结着青南瓜么,正好给鸡羊吃吃。冬天大雪当里,叫了一起闹闹热热去果园整整枝,整枝么,勿要早,否则天气暖时整,要缩芽个,水分跑脱个呀,树也像动物会冬眠个,就在果树困觉时整,整得一人一手高,这样子采摘勿用爬梯子凳子。到了春天当里,各样果树开花,跑到果园就像跑到仙境,开心!”
我听着这农妇朗朗然的一通果园经,但觉脑洞大开,恍然穿越到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我们见惯了车流用惯了电子刷惯了硬卡,不间歇地被绑架着消费,攀比,已经渐渐开始腻烦这些貌似便捷,却被褫夺了与自然亲近的生活。眼前此景,耳畔此语,这样原朴又蓬勃,着实惊艳了我的感觉,痴想或许也可在某时安营扎寨于此地。
然,悄悄是别离的笙箫,采风行程时间的制约,当得先作别这方水土这方人。
这一行嗟羡着稼穑田园之事的人儿,重新返入果园村入口处的清河码头,开启归程,可是我的心为何这样喋喋不休,频频回首。
码头的里边,不正是我们苦心孤诣想要的“当下”的快乐和自在么?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于天地间,四体皆勤则四季皆新,不去贪心不足蛇吞象,遑论哀怨嗔痴自扰殇。
果园村的村民在大时代中拥有着自信的守望,擅作浑然天成的掌上之舞,顺天而行,合乐而歌,难道生活的本来面目不就该这样清新简约而乐活?
惠萍 一个动人的名字(组诗)
陈陌
序
我曾无数次在你面前经过
你只是我从一个家走向另一个家
中途的路标
我也曾无数次在你面前停留
却不知你的命名
原来是为了纪念一个人
(一)名称的由来
朱慧萍
一个出生于崇明的小女子
跟随参加革命的丈夫
来到了启东这片新土
用青春书写了壮丽的人生
用热血谱写了动人的乐曲——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
为了百姓的生活幸福
将年仅28岁的生命
定格在惠安镇碉堡的西窑里——
从此
你让这片新土
有了一个动人的名字
(二)璀璨的明珠
三十年前,你只是村里的一个小作坊
三十年中,你曾一度改制歇业
三十年后,你引领中国润滑行业
是什么,让你不断蓬勃发展
是什么,让你奋力走向辉煌
2015年八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走近你
看到你三百亩的占地面积
看到你高大、现代化的厂房与办公区域
看到你车间柱子上丰富而有内涵的标语
我一下子明白了
一个企业走向成功的秘籍
你是惠萍镇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穿梭在你的胸膛里
听火花飞溅中发出的滋滋声
我凝望着那一句动人的话语——
用我们的智慧和信誉雕塑顾客的满意
无言的感动
便于刹那间 升腾而起
(三)寂静的故居
这里的每一个白天和黑夜都是寂静的
唯有风 自由地
拂过紧闭的木门
吹开沉寂的时光
这里所有的植物都是寂静的
树木郁郁葱葱 草儿绿得发亮
幽绿的苔痕
映刻在青砖路上
这里所有的建筑都是寂静的
旧式的“三厢房” 穿斗式两层楼房
院中的一口古井
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我是这里不经意的过客
我也是寂静的
我步履轻盈 心怀幽想
用满腔的柔情
和花草树木一道
默默仰望
(四)水果小镇
这是哪位神仙的一大手笔
将两千四百亩土地装饰成绿地
再在中间镶上竹篱笆长廊
让我们的笑脸
辉映夏日灿烂的斜阳
梨树一棵挨着另一棵
葡萄一藤缠着另一藤
八月的微风穿过屋角
田间的小道向远处延伸
传来采梨老人欢声飞扬
品尝随手采摘的香梨
行走在竹篱笆长廊
丝丝甜蜜 阵阵惬意
恍若间
竟让我忘记了时光
结语
我惊叹你有金牌企业南方润滑
我惊叹你有古色古香的沈轶公故居
我惊叹你有独特的水果小镇
我惊叹你有水上休闲的大自然度假村
我惊叹你有沾满历史烟尘的惠安老街
我惊叹你有世界之最的金鱼草陶瓷
我惊叹你有香火旺盛的大雄古寺
但我更惊叹——你有一个动人的名字
在九月,我抛弃所累心思简单
静静地,从你的名字一直写到了迷人风光
立秋以后的阳光
唐诀心
立秋以后,阳光开始斜照
像一头金黄色的豹子在寻找
奔突的角度
为此,发出粗重的喘息
它携着依旧逼人的热浪在风中
奔跑,谁也拦不住它
它周身蕴藏无穷的力量
可毕竟立秋了
天边似有南归的大雁飞来
这只充满野性的豹子
开始在金色的稻田上温柔打滚
眼里露出丰收和善良
当它从我的眼前跑过
奋力推开我发梢上的炎热
在我内心留下一片蔚蓝的辽阔

野花(水彩) 朱海燕
老房子
陆汉洲
这些年我回乡下老家——惠萍镇南清河村,落脚的地方就是我大哥家。大哥家楼房的东半部分,原先是我的老房子位置。
我从部队转业后,一家三口都进了城,难得回一趟乡下老家。眼看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残瓦破壁,透风漏雨,一年不如一年,我便生出了将它卖掉的念头。于是,后来就以800块钱,象征性地卖给了我大哥。卖掉老房子,我并不是图钱,而是图个省心省事。
对此,妻子埋怨我草率。800元钱如今算什么钱,可是老房子说没就没了。虽然大哥大嫂一直对我们不错,但落脚的地方毕竟不是自己的家。老房子虽然破旧,但毕竟是属于自己的一个窝。
我家的老房子共两间,建于1977年,砖木结构,五架头,井深5米多,西房间是传统的丈八筒(4.8米左右),东边的厨房和吃饭间略小。那年,我还在部队。房子是在父亲手里由大哥具体张罗着盖起来的。
在村里头,我家的经济条件属中等偏下那一类,我在部队提干以后稍好一点。但盖这两间房子的钱,基本上都是我从部队寄回家的。父亲在收到钱后,这一回买一点砖头,那一次买几片瓦,接下来再买几根桁料木头。房子盖好,欠人家的工钱,最终还是我掏的钱。反过来说,没有结婚成家,我的钱就是父亲的钱。而且,又是为我盖房。
按建筑物竣工的基本标准,当年,我那老房子只能算盖起来了,而不能说盖好。严格地讲,竣工条件不具备。因为没钱,厨房间的四壁还没有粉刷,红砖和泥浆嵌缝的墙壁,裸露着不文明的身躯。因为买不到木料,厨房间前面的窗户只有带有个木栅栏的框子,而没镶上玻璃的窗。1978年元旦我结婚时,那扇窗户上就挂了一张芦苇席子。
这是比较寒碜的两间老房子。妻子曾提出最好不用水泥制品桁料,这两间房子便都用木头桁料,由于木头细,两间房子中间都用了钢筋“人字梁”作支撑。更为寒碜的是,外面厨房间的橼子,三三两两地夹杂几根小毛竹杆子。房子盖成之初,在外头看,屋面的瓦楞还是齐齐刷刷平平整整的,而日子一长,用毛竹杆作橼子的地方的屋面,明显塌陷下去了。
尽管如此,这经典的寒碜老房子却曾经是我的一个温馨的港湾。我在那座老房子里结婚,两年后,又在那座老房子里生下了我们的儿子。妻子是位教师,在调入部队之前,她平时住校,节假日里,总要回老房子住住,洗洗,整整,晒晒。春节前,学校正放寒假,她一接到我探家的电报,便开始搬着指头算我到家的日子,到了那天,她总会站在老房子门口,微笑着向不远处的东头的村口张望。1982年冬,我们的儿子小炜已经2岁了。这一个春节,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老房子过的最后一新年。第二年暑假,妻儿就随我调至山东我的部队驻地工作。四年后转业,一家三口即进了城。
老房子已经在我眼前消逝近二十年了。如今,老房子只是我过去的一个梦。今天,我站在大哥家的场心里,只能从楼房东半部分,寻觅老房子的影子。
记忆中的味道
郁煜淑婷
夏日中,连续的高温总是让人毫无食欲。而每每这个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浮现的会是那淡淡香味,来自记忆中面饼的味道。不知为何,那种味道在我脑海中时常挥之不去,而且与家乡启东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面饼,对于启东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夏季食物了。对我来说,也不例外。在我的记忆中,这也许是记得最清楚的味道,尤其是联想到夏天的时候。
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着外婆去买菜。外婆常去的是她家附近的一个小小的菜市场。一来二去,菜场上好些卖菜的、开店的都认识我了。而面店的老板似乎特别喜欢我,他们家除了卖面粉、馄饨皮、饺子皮、面条之外,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现摊现卖面饼。面店老板每当看到我,都会笑着递给我一张刚出炉的面饼。即使没有任何的菜可以卷着一起吃,但是当我闻着淡淡的面饼香,轻轻地咬着,就觉得很满足。
每当家里要吃面饼的时候,外婆就会去面店里买。但她可没有心思等待着面饼一张张做完,总会先跑去别的摊位买些菜,而我总是饶有兴趣地站在面摊前看着面饼一张张地摊出来。其实它的做法和别处常见的煎饼果子做法相类似。但煎饼果子是脆脆的,面饼摊出来之后会不一样,有着独特的柔软和劲道,甚至还有些透光的感觉,看着就舒服。
夏季中特有的面饼不仅是日常吃食,更是家庭聚会中用来招待客人的好东西。它也许是启东人关于夏天的独特记忆。对吃特别有兴趣的我,非常热衷于看红遍大江南北的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前两部中领略过好多各地美食后,心中更期盼的是家乡的特色美食也能出现在其中。听说,《舌尖上的中国》第三部中可能会出现面饼的身影,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十分盼望能早点在荧幕中见到自己喜欢已久的家乡食物。
吃面饼时,往往要做一大桌子的菜。好些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印象中只能在启东才能吃到的菜,比如:凉拌金瓜丝、韭菜炒绿豆芽、咸鸭蛋拌豆腐、烂茄子、咸瓜炒洋扁豆……取一张奶白色的面饼,随意夹几筷子自己爱吃的菜,慢慢地卷在面饼里。面饼一般薄薄的,所以能看得见包在里面各种菜的颜色,挺好看的。将喜欢的食材包在面饼里,都会有种很可口的味道,而且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配方。每个人卷出来的面饼,都不会产生相同的味道,这就是它的奇妙之处。我总感觉面饼好神奇,它似乎能包容一切食物的味道。
即使我身在他乡,普通话还算说得标准,但事实上,我从未忘记过家乡话,以及关于家乡的全部印象。不在启东的日子里,爸爸妈妈总是要求我讲启东话,怕我太久不回启东会忘记乡音。但我觉得,我应该永远都不会遗忘启东,以及和启东有关的一切。就像记忆中的面饼一样,不仅卷住了美味的家乡美食,也卷住了热爱家乡的心情!
尽管炎热的夏天本就不是什么有胃口的季节,但是简单的面饼卷上几样清淡的小菜,顿时就会让人胃口大开。记忆中的味道,被记住的不仅仅是夏天的特殊食物,其实还有我最热爱的那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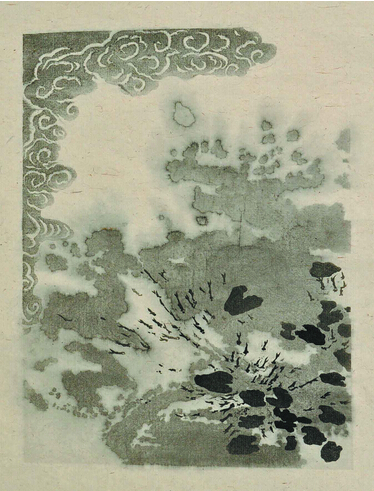
游艺 (版画) 朱燕
蛙鸣
施勇
傍晚的时候,一场猛烈的雷雨倾注于我所居住的这座小镇。它让我领教了光阴被压缩的巨大力量。我透过玻璃窗,眼看着小区东侧的一片正待开发的茅草地,在混沌之中逐渐模糊了轮廓,继成汪洋。似乎从桑田到沧海不需要千年,只一刻钟便够了。
雨后散步,路过那片汪洋,忽然听到了蛙鸣。先是怯生生的一两声,“咯咯、咯咯”,声音来自于水中,待要寻去却没了声息。心想是不是听错了,“咯咯”声却又起,是在距我五步之遥的一丛水草间。音调似乎与第一次的有些差别,显得老成而又低缓,如吸着水烟的老者笃悠悠地向小辈们叙述早年的往事。紧接着,仿佛一下子被唤醒了似的,东边、南边、北边,甚至在我所站立的岸边都响了起来,“咯咯、咯咯、咯咯”,几乎每个角落、每块泥土、每片水域都有声音发出,像是在附和老者的教导,又像是展开热烈的讨论。蛙鸣声将我包围,又将我托起来扔回到小学时代,让我置身于晨读时的乡村课堂,耳边回荡起同学们没心没肺的朗读声,毫无章法却充满着生机。
仔细听,有清越似歌唱的,有激昂如朗诵的;有漫不经心东扯一声西喊一嗓的,像在打瞌睡的;有急促得如做道场僧侣在念《金刚经》的。音调音色不一而足,掺杂着偶尔路过的行人咳嗽声,结束了晚自习的少年骑车辗过潮湿柏油路面的“沙沙”声,和远处汽车掠过街道的呼风声。林林总总汇成了一个小镇的夏夜。
很奇怪,蛙声如此热烈,我却丝毫不觉得聒噪,心神反而安宁了许多。这蛙声让我想起乡下的老宅。这个时辰,父亲一定吃过了晚饭,与东宅的范家伯伯在屋前场地上,边乘凉边闲聊。这蛙声还送我回到了儿时,露天的饭桌上已撤去了碗筷,我爬上桌子仰天数星星。宅前屋后东西泯沟,蛙声一片,我在这蛙声中恍恍惚惚入了梦乡。醒来时,蛙声依旧,只是身上多了一条薄毯,是母亲为我盖上的。在这亲切的声音中,不论是睡去还是醒来都是幸福的。
茅草地原本寂静无声,一场雷雨造就了蛙声鼎沸。雨走了,青蛙们留了下来。
乡情乡味
黄向东
一年四季,难有机会出去游玩,这说走就走的乡村之行,便成了我们的钟爱。
要说缘由,旷野悦目、清风拂面均为引力,但令我们欲罢不能的还是那份浓郁的乡情、甘醇的乡味。
乡下,有不愿进城的、妻最牵挂的、我的岳父母。岳父是乡村教师,已退休数年;岳母超龄坚守赤脚医生岗位,仍敬业如初。但岁月不饶人,日见衰老的岳父母,最盼天伦之乐,故需子女常去探望,这是我俩的责任。有道是,百善孝为先,尽孝不能等。另一诱惑,就是常能享受一顿绿色大餐。空余时间,二老在宅后的三分地里下足了心思,精心栽种出四季菜蔬,鸡笼里的数只土鸡更被伺候得积极下蛋,左邻右舍也常会送来一些时令。于是,定期到岳父家“饱口福”,基本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固定活动。特别是在春夏两季,各种菜品最为诱人,什么香沙芋烧青毛豆、香沙芋炖家户鸡、韭菜炒土鸡蛋、西红柿蛋汤、辣腌小黄瓜等,都是妻儿认定的佳肴。我尤爱炒青蚕豆,每次来上一大盆,而后倒上一碗传统配方酿造的东疆米酒,送到嘴边酌饮一口,“吱”的一声,哧溜穿喉进肚,瞬间通透血脉,再夹上几粒炒青蚕豆,嚼得满嘴溢香,已然不屑玉液琼浆、山珍海味,怎一个“爽”字了得!
乡下,还有滋养了我二十载的老屋,常回去瞅瞅,常是回忆翻涌。我的父母十余年前进城做小生意,早随我们住一起,但老屋留给我的儿时乐趣,怎能随便忘怀?曾记否,每当炊烟升起,总让我口水窜出。在物质生活较为贫乏的七、八十年代,吃最为简单,但至今让我念叨。那时的一日三餐,都是父母自己栽种的五谷杂粮、家常蔬菜,简陋烧煮而已。若想解解口馋了,大人、小孩齐动手,就地取材自制工具,到河沟里钓起鱼虾,到夏天更直接,跳进水里用手抓,注定足够全家人饱餐一顿。待到傍晚,多是母亲一手张罗,清煮或红烧上桌,而后任我和妹妹一顿朵颐,那份惬意难以形容,至今让我梦里追寻。幼时,我不明白父母为何只吃“边角料”,常在一旁端详、一脸愉悦,就像现在儿子不明白我们一样,如今早已明了。要说老屋里最值得珍藏的东西,还是我在煤油灯下做家庭作业时,陪伴一旁的母亲常对我的念叨,“想过好日子,要好好念书;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拿,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一生一世有得吃!”母亲没多少文化,但懂做人的道理,小时候我不太理解,只晓得听话没错,现在想来那真是影响我一生的教诲,朴实却管用。
乡情难忘,乡味难舍!曾经,它哺育我健康成长;而今,它滋生我的念想。我愿,退休后住回乡下去!